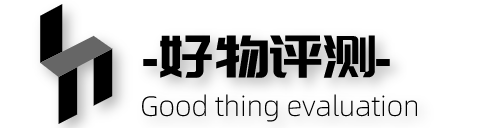获奥斯卡编剧奖的《虎豹小霸王》:新好莱坞时期西部片的另类尝试(电影西部片虎豹小霸王免费观看)
文:宿夜花
圣丹斯国际电影节,由好莱坞著名影星罗伯特·雷德福创办,是当代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“独立制片”电影节。它不仅为厌倦了工整精致、刻板模式化商业大片的观众,提供了很多更具锋芒与探索性的“作者电影”,更为年轻导演进入主流视野提供了一个跳板与舞台。
而关于圣丹斯(Sundance)名字的源头,却鲜有人知,这源于罗伯特·雷德福其演员生涯最具影响力的角色——《虎豹小霸王》中的“Sundance Kid”(太阳舞小子)。电影《虎豹小霸王》(又译作“神枪手与智多星”),不仅获得了第42届奥斯卡的最佳原创编剧奖,更入选了2008年由美国电影学会(AFI)甄选的西部片TOP10的第7名。
如果说一部电影时下的高口碑与票房,是当代观众最直观、最感性的反馈;那么一部影片后世的高度赞誉,则更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,是经历了时间的筛选、大浪淘沙般的淬炼
当电影爱好者谈论起《虎豹小霸王》,最典型的形容便是——“新好莱坞时期”(即60年代末到70年代)西部片的反类型尝试。由此可见,当代人的视角下,影片既有其对于西部片类型发展史的标杆价值,也有作为好莱坞新浪潮阶段内的时代意义。
60年代,是好莱坞传统西部片的衰落期,为了对抗电视对观众的吸引力,大片厂不惜花费巨资制作各种类型的“宽银幕”史诗巨制,约翰·福特的《西部开拓史》正是这一时期的西部史诗代表,但主题的陈旧、形式的保守,仍旧无法满足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。
传统的西部片中,主题可见于如下几类:
霍华德·霍克斯导演的《红河》,讲述着传统与现代、荒蛮与文明的冲突;
弗雷德·金尼曼执导的《正午》,以匡扶正义的孤胆英雄处境,反映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过渡到现代法治文明阶段的过程之阻力;
约翰·休斯顿的《碧血金沙》,揭露了开拓神话、淘金寻宝的行径背后,人性贪婪、嗜利、自私的丑恶面。
而60年代后期,观众似乎看到了披着文明外衣的“良善与正义”,背后实则是对腐朽、僵化秩序的粉饰与包装。时下的战争,摧毁了过往陈词滥调构建的梦幻乌托邦,激发了反叛情绪;各种风起云涌的反思浪潮、摇滚嬉皮文化的流行,让观众发现传统秩序的种种痼疾。观众亟需从电影中看到更多鞭挞、批判、反思,而非粉饰、虚掩、避重就轻。
因此,1969年乔治·罗伊·希尔执导的《虎豹小霸王》,与同年萨姆·佩金帕的《日落黄沙》一起,从内在把握到了新一代观众观众的精神需求与价值观,拉开了“新好莱坞时期”反类型西部片的序幕。与此同时,法国电影新浪潮、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对年轻一代电影人与观众的审美带来很大的影响,这也反映在这一时期电影的风格特点上。
它们与《雌雄大盗》、《逍遥骑士》一样,成为诉说“垮掉的一代”青年人追求自我、释放个性、反抗陈规、冲破旧秩序桎梏、摆脱僵化思想束缚的突破意义之作。
“英雄神话”的颠覆与“反英雄”形象的构建
不同时代的观众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是不同的,战后成长的新一代青年,已经没有了对“西部”生活的直接体验。那种开荒拓蛮、与自然搏斗中张扬的生存意志与英雄气魄,纵使仍旧不乏感染力,却再难令年轻观众感同身受。无论是《搜索者》中的约翰·韦恩,抑或是《正午》中的加里·库柏,其形象或多或少都是“英雄神话”的写照——英勇、无惧、正直、坚守。
《虎豹小霸王》的两位主演保罗·纽曼与罗伯特·雷德福,恰好是由传统好莱坞过渡到新好莱坞时代的明星,他们形象上仍具有经典英雄的品质——强势、自信、勇猛,但又多了几分玩世不恭与游戏人生的离经叛道与潇洒不羁。因此,他们来诠释影片的时代内核自然是精准无误的。
电影《虎豹小霸王》将时间聚焦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,此时美国的工业文明迅速成熟,瓦解了孕育西部英雄的土壤,那些为老一辈所津津乐道的侠盗、枪手、匪寇、亡命者,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走向消亡。
这种文明更替的必然性,造就了昔日英雄难以与时俱进、无所适从的处境。影片没有选择以一种凄凉、悲壮的口吻谱写一曲西部时代挽歌,而是用戏谑、幽默的喜剧风格揶揄、调侃主人公这种尴尬处境。
布奇·卡西迪(Butch Cassidy)是一个以现实人物为原型、符号性很强的名字,象征着威震四方的西部侠盗;而太阳舞小子(Sundance Kid)——“太阳下翩翩起舞的人”更是一种原始生活印记、生存方式的隐喻。两个旧时代的英雄,在新的文明世界里只得亡命天涯以逃离追捕。
布奇·卡西迪,虽然作为一方侠盗头目,却与西部神话中的英雄形象大相径庭。看似是“智多星”,却闹出用炸药炸得钞票满天飞的困窘尴尬之事;他无法使得他的手下信服,一直处于被挑衅之中;他没有好枪法,甚至都无法在生死殊博中发挥作用。他的智谋仅仅是比同伴太阳舞小子多一份圆润与变通、豁达与机灵。
太阳舞小子,作为“神枪手”,却不会游泳(意味着应对环境变化缺乏适应力、没有与时俱进的能力)。他外形冷峻、强势,身手矫健、迅猛,具有十足的英雄范儿,却思维简单、缺乏远见卓识,他的生活没有更远的目标,只得在同伴智多星的指引下,进行漫无目标的逃亡之旅。
他们的笨拙、尴尬,荒谬不经、笑料百出的背后,西部英雄形象得以彻底解构。所谓的“智多星”和“神枪手”是特定阶段的英雄,而伴随着时代变迁,他们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落伍的尴尬处境之中。而“反英雄”的魅力正在于,在消解英雄的伟大与崇高之后,展现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尴尬、无奈、无所适从与无可奈何。
一场无望的逃亡,一场徒劳的反抗——“新好莱坞时期”电影人的自嘲与思考
他们的逃亡生涯里,还有女教师埃塔的陪伴。因此,双雄间的男性情谊,又被女性角色的加入打破。这种关系有点类似于弗朗索瓦·特吕弗《朱尔与吉姆》或后来吴宇森《纵横四海》里的周润发、张国荣与钟楚红。
比起心理层面的刻画,影片更注重角色的象征意义。知识女性与自行车,所寄托的正是一种新的文明世界的精神生活。女教师埃塔,自身的纯洁、天真的秉性是文明世界呼唤的一种理想化行为规范的代表,她远离西部男性世界的枪林弹雨、烧杀掠夺,通过学习知识、了解现代文明的准则。
而自行车,更是影片很关键的一个符号意象。自行车取代马匹的过程,不仅仅是文明发展给人的生活方式带来的改变,更意味着一种精神世界的改变。智多星与埃塔骑车游乐的一场戏,无疑是影片中最为浪漫、轻盈、诗意、纯净的时刻,在这一瞬间,智多星布奇,放弃了戎马江湖、刀枪交战的快意恩仇之乐,融入进了现代文明的规范之中,这正是影片所反映出的一种时代的精神转变。
对比影片与60年代末“新好莱坞时期”的其他经典作品(诸如《雌雄大盗》),它们所传达出的困境总是相似的:即是说如何在颠覆传统、打破陈规后去建立一种新的平衡?
《虎豹小霸王》中,智多星与神枪手所代表的是旧的秩序下所造就的迟暮英雄,他们所代表的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形态,注定会随着文明社会的到来而随风而逝、消解在历史的大舞台中。
《雌雄大盗》中,邦妮与克莱德是僵化的机器牢笼的反抗者,他们打破陈规桎梏、试图寻找一种内心的自由与个性的释放,却终究陷入一种虚无,最终用死亡终结他们的离经叛道之旅。
结合更多的好莱坞新浪潮作品来看,无论是古典题材所呼唤的和谐、静谧、安详的原始田园世界,还是盛行的“公路片”所影射的未知的前方、一种反叛所有世俗枷锁后所到达的一种绝对自由的世界,都是两种方向上的“乌托邦”,是两种无法达到的想象世界。
因此,无论是反抗传统追求自由,抑或是回归田园沉溺过往,都是无望与徒劳的。时代的变化,需要每个人在不断地认识世界、适应文明的过程中做出妥协与改变。所以,《虎豹小霸王》与其他更多好莱坞新浪潮作品的魅力,仍旧不会消退。
因为,比起确定的结果,青年人更需要在不可捉摸的未来中去实现更多的可能——无需因循守旧、固步自封、沉溺过往,亦无需过分迷茫、困惑,在不断反思与创新中无惧无畏地探索出自己的道路。